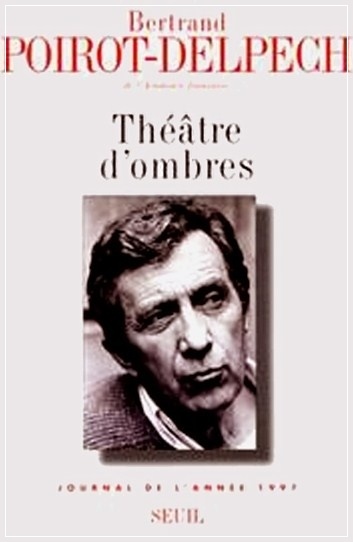香港下一代四個現代化 (1) —— 遲敬意 (丘世文) 1981 年 11 月 號 外

我們不能明白下一代,正如我們的上一輩當年不能明白我們一樣。
如果當年伯父輩的人們能義正辭嚴、理直氣壯責備我們大逆不道,那麼我們卻享受不到這毫無疑問的特權 —— 因為,正如下一代,我們也是叛徒。面對二十歲剛出頭的小伙子們,無論他們如何素隱行怪、標奇立異,當我們撿起石塊想群起而攻之的時候,心裏總禁不住遲疑 —— 也許,始作俑者的就正是自己 —— 誰膽敢拋擲第一塊石呢?當我們是廁身在玻璃屋裏,腳踏在動搖的基礎上?
對抗或接受是個人道德上抉擇的問題,但首先我們總得設法明白 —— 我們的下一代將會有甚麼顯著的不同?
基本上來說,我們的下一代與我們當年是一致的,然而我們不能接受的,是他們將會把叛逆的精神推縯到連我們也為之震驚的邏輯終結去。
文化: Anything Goes
多蒙中國近百年的內憂外患,新文化運動以來知識份子一直都盤旋不離幾千年來正統的金科玉律:任何形式的藝術,價值準則總在於能「經國濟世」與否。我們的上一代承襲了五四的叛逆形式,卻從沒有繼起了五四的創新精神,這一點我們是有目共睹的。我們的上一輩並沒有擺脫前五四時代的舊式道德主義的包袱,把孔家店拆毀後卻急於恭奉三味書屋,把古文廢除後卻把第一代的白話尊崇為新文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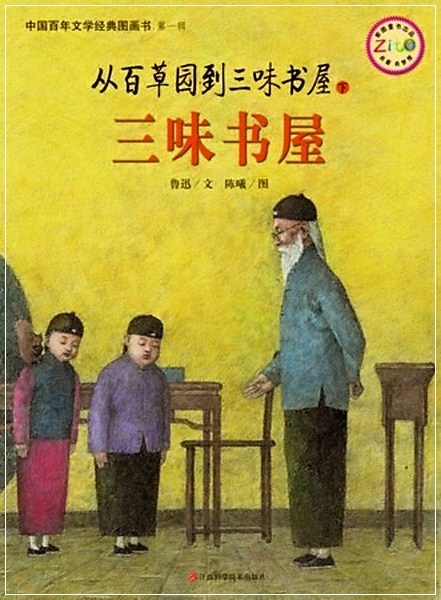
我們當然可以看得清楚,上一代的所謂新文化,不外還是一小撮(以七億人口作比率而言)知識寡頭份子把一種獨裁專政取代另一種獨裁專政而已。文化始終沒有普及化、多元化、廣泛化過來。常見上一代文化人總不自知地犯著老八股的毛病,時至今天仍理直氣壯埋怨歐風美雨的壞影響、指控年青作家寫不是中文的「中文」,滲雜俚語和外語句法等。我們能夠明白這類操之過急的實用文化論者的苦心 —— 純淨制度化文化,天下言同聲、書同字,天下一統以達治:這是歷來知識份子救世救民的一廂情願簡單公式,也是知識份子總不自知地淪為政客幫閒的原因。
因此,早期香港知識份子界始終是活在稔熟的世界中,隨著兩條我們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路綫邁進,毫無片刻岔路上的疑惑的:本地公務員有如科舉制度晉身仕宦之途,擠身不進或因文化先決條件所限的,還是依伴了舊傳統的支柱,憂憤莫名,評擊弊政(以早期香港殖民地主義代入。)但我們可以斷言,如果後者成功執政,還不外是來一場打倒你,我來做,另一政權的官式文人而已。我們,總沒有堅待不肯仕宦、更不隱居避世,忠於文化本質上不應有一統、永遠多元辨證的新文化人的。

金 庸
如果舊一代活在變化遲滯的時間,看不出白居易為外地傳入的琵琶淚濕青衫就有如我們當年為歐西流行樂曲瘋狂的無可厚非,那麼我們卻因現代急劇轉變把歷史壓縮呈現而有倖看見金庸從雜家九流被捧而成研究對象、文化明星、兩岸政要接見的上賓;我們喜歡與否早已接受了李小龍是文化現象、電視長劇是移風易俗的媒介,三毛、瓊瑤、依達小說也是文學其中的一種表現。我們開始懷疑,凡是影響力,不能漠視的文化活動,也許就無高下之分,而只有不能不認識的需要吧?
沒有人敢跨時代妄下定論,但肯定的是今後香港文化準會如西方先進國家那樣步入莫衷一是,文化無政府的狀態。下一代將會變本加厲昇天入地球之遍找尋萬千種連我們也不敢接受的文化表現形式獨據一方,與其餘文化流派分庭抗禮。
“Culture is an area where there can never be a good leader unless each man is his own,” Bertrand Poirot - Delpech 說得好,但隱伏在我們意識下的恐懼,卻是有朝這句話會成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