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到荼蘼話亦舒 —— 陳輝揚 1986 年 4 月 號 外

當初只看衛斯理﹐從《透明光》、《不死藥》、《藍血人》、《屍變》、到《迷藏》、《地圖》﹐都是在傳達書屋看的﹐看得很快﹐一來心急﹐二來時間匆匆﹐無暇細讀﹐那時亦舒作品結集的﹐大約只有明窗出版的《風信子》及《喜寶》﹐還有一部《我之試寫室》。天地的「亦舒系列」尚未開始﹐但亦舒風潮似在醞釀中。
五六年來﹐衛斯理看了五六十部﹐亦舒作品亦看了六十部﹐兩兄妹的文字﹐合計不下一千萬字﹐等如看十次《金瓶梅詞話》或兩次《蜀山劍俠傳》﹐自己都不明白如何會看了這百多部小說及散文。衛斯理想像力超凡﹐文字平凡﹐他有不少地方脫胎自還珠樓主﹐但他取材現代科技再以自己的人生觀鎔裁治鍊﹐成就了一匪夷所思的幻象空間﹐近作《遊戲》是他近五年來最佳作品﹐取意深﹐佈局巧﹐透視人情入微﹐為中國科幻小說的經典。倪匡若不是刪改續寫《蜀山劍俠傳》﹐我不會如此反感;續作無可厚非﹐惟盜名 —— 將《蜀山劍俠傳》強改為《紫青雙劍錄》則絕不可諒。話分兩頭﹐倪匡的「衛斯理系列」已是中國科幻小說的里程碑﹐至於「原振俠系列」能否有新突破則拭目以待。而當代香港文學史上﹐若選三個最受讀者喜愛的作家﹐除金庸外倪匡及亦舒可說穩坐第二三位。衡量一個作家﹐讀者的數量及質素同樣重要﹐張愛玲可為代表 —— 只見張迷有增無減﹐當《半生緣》邁向第二十版時﹐我相信張愛玲確與兩代的讀者有相知﹐而亦舒從張愛玲的讀者到目前最具叫座力的作家﹐中間一段歷程﹐也就反應了香港文化二十多年的變遷﹐在亦舒那一輩女作家中﹐蔣芸、陸離、西西等各擅勝場﹐但就歷年產量及密度而言﹐亦舒為此中翹楚。
「女人是一本活到老學到老的書﹐有心人才會懂一點……」
--- 蔣芸
亦舒的成就建基於她對女性心理的了解﹐她的文字不長於分析﹐亦不長於描繪細節﹐而擅長於營造人物生活的氛圍 (mood)﹐也就是一種與生活肌理相應的感性﹐是這一點使她屹立於文壇而不倒﹐當然個人背景有很大關係﹐她出生於中下階層﹐文思早熟﹐經歷記者生涯﹐一面儲蓄到英國留學﹐感情上的離合﹐以致職業女性面臨的大部份問題差不多都有一定經驗﹐她可說是香港一部份女性成長歷程的縮影﹐只不過她反省的範圍更深更廣。

有太多人太急於為「流行作家」定位﹐從「文學批評家」到書店售貨員﹐都認為自己有資格視某些流行作家的作品為垃圾﹐有些知識份子則以不看某些作家如亦舒的作品為自我標榜以至「自我肯定」的手段。
如果未看過亦舒﹐請那些「文評家」閉上尊咀——沉默是金。縱然亦舒現在寫的雜文很差﹐亦不必影響我對她以往表現的評價﹐正如我不會因二十年前那部《女記者手記》的文字拙劣而否定她後來的進步。倪匡在《我看亦舒小說》所說的話﹐不體不差﹐他以內行人提供讀後感﹐不能算嚴格的批評﹐但書中討論《喜寶》、《蝎子號》及《風信子》都近情理﹐對亦舒的小說世界亦有一清澈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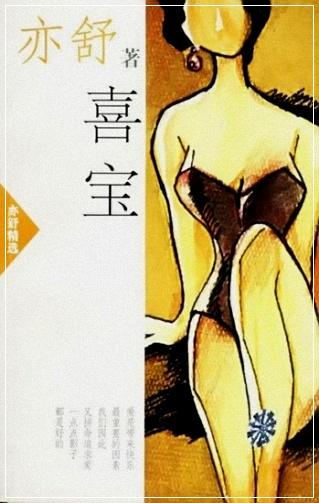
亦舒的散文不及小說受歡迎﹐這其實有點怪:論文字﹐她的散文更精練﹐見解更「到」;而對某些題材的見解更加精深﹐如《剎那芳華》談《紅樓夢》﹐有一篇「千元千字」談平兒﹐一針見血﹐是紅學家忽略了的沃土。就我看﹐一般讀者醉心於亦舒兩方面的才華:首先﹐她的故事滿足一般人的幻想﹐家明與玫瑰以至丹薇都是所有人欲求的對象﹐﹐知識水平並不能改變這種幻想﹐只不過知識份子更難滿足這方面的需要。其次﹐她的筆觸及佈局﹐這是她短篇小說成功的主因﹐從《家明與玫瑰》、《藍鳥記》、《囘南天》、《五月與十二月》、《今夜星光燦爛》、《偶遇》以至《阿細之戀》等廿多部短篇小說集﹐人物情節大同小異﹐有些題材如離婚﹐母子﹐家明與玫瑰及婚外情﹐都有重重變奏﹐貫穿其間的是亦舒對城市生活及感情關係的不滿及不甘﹐不但是對物質生活的爭取﹐也充份反應人際關係的不定性。亦舒既不甘於如職業文人埋首寫稿﹐又不甘如家庭主婦隱姓埋名﹐只好一手執筆﹐一手持家﹐以職業女性的姿態「打天下」。是這一點耿介﹐使她的小說吸引年輕女性﹐她們不在相信白馬王子﹐但她們希望做子君﹐唐晶﹐哀綠綺思﹐喜寶以至玫瑰﹐她們相信這一代的女性可以有自足的生存能力﹐亦舒小說世界強調競爭﹐女主角以意志改變自己的命運際遇﹐男性形象不外幾大典型:大學生、大學教授﹐尋不著玫瑰的家明﹐事業成功的專業人士﹐與那千變萬化的女性眾生相一比﹐不禁相形見拙﹐在這一堆男人中﹐有心人很有限:他們總是問題的根源﹐却又無法合理地解決各種難題﹐他們永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局。

很多人說亦舒雜文喜歡罵女人﹐其實她罵男人更「到家」,她執持一套看似傳統的價值觀來衡量這城市的男人﹐不合格的佔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餘百分之三是有志於「獨身」的專業人士﹐百分之十已「名花有主」﹐其餘的大概是同性戀﹐離婚獨居的知識份子﹐科學家、講師及教授等。亦舒小說世界的好男人原是滄海遺珠﹐出身、財富、學識、常識;文可以看《紅樓夢》、《魯迅全集》、《小王子》《兒童樂園》及金庸與張愛玲全集;武可以在實驗室做粒子加速運動的實驗﹐這樣的男人當然不易找﹐他們是知識份子中的精英﹐貴族中的貴族。倪亦靖大約是少數合格分子﹐早期作品裏的家明只怕亦要「出局」﹐除非他去讀 post-doctorate 的研究學位。這種極端「理想化」的男性形象﹐是亦舒執著十多年的理念﹐刺激她創造這許多超凡入聖的女性形象。
亦舒從事創作二十多年﹐最令人激賞的應是她的文字。一般讀者大概認為她文字流暢﹐不以為奇﹐事實上﹐在近十年的小說創作上﹐她的文字最平淡自然﹐也就是耐讀。她的散文最見本色﹐《自白書》為經典﹐集中佳作如「歌星們」、「同性戀」等﹐詞鋒犀利﹐咄咄迫人。在《退一步想》中﹐「不要」﹐「大方」的見微知著﹐「三不看」談看小說﹐「五十年」寫父母﹐「承繼」的自由﹐以至「偶遇」寫姊弟情的結句:茫茫宇宙中﹐我們是姊弟﹐簡短精采﹐文字極度濃縮﹐實在是「方塊文字」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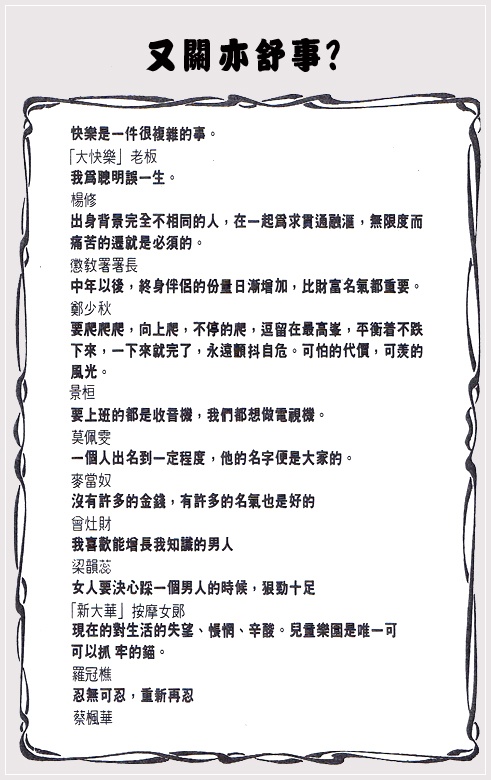
套用亦舒金句於 1986 年的香港
先說長篇小說。
亦舒長篇小說在進步中﹐除《玫瑰的故事》及《喜寶》﹐她的前中期長篇通病在於「爛尾」,這是她在佈局上的致命傷﹐連《我的前半生》亦不例外﹐就人物而言﹐她寫長篇較短篇好﹐但不一定及得上她某些中篇。至《朝花夕拾》她才對佈局有較精巧的設計﹐時空交錯的技巧雖不新﹐亦可謂中規中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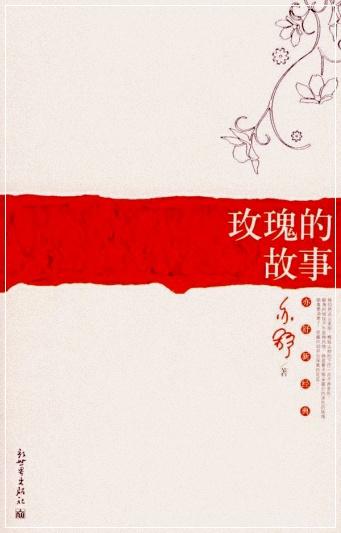
若選三個長篇代表﹐我想不離《玫瑰的故事》、《喜寶》、《我的前半生》、《開到荼靡》及《朝花夕拾》。《玫瑰》的佈局最別緻﹐但心裡描劃不夠深刻﹐是入世未深的少作;《喜寶》寫忘年戀不及寫女性對物欲的傾心——女人當然可以對蘇格蘭古堡傾心﹐但姜喜寶是亦舒小說中最難忘的女人;《我的前半生》寫涓生﹐子君與唐晶﹐最有回味不是子君﹐而是唐晶的獨來獨往﹐《開到荼靡》是亦舒野心最大﹐力圖使人物最有「深度」的作品﹐但書中寫同性戀太牽強﹐寫男女主角割脈自殺都太浮泛﹐是一部瑕疵極多的佳作﹐《朝花夕拾》是她近年結構最佳的科幻小說﹐雖有太多《回到未來》及衛斯理的影子﹐但寫情卻不乏動人之處﹐文字亦簡鍊。這五部作品各具特色﹐可管窺亦舒在長篇創作上的成就。

又如《香雪海》寄情無地﹐《獨身女人》的無奈﹐《野孩子》的父母情結﹐《她比煙花寂寞》的姚晶——一個婚姻失敗﹐死得莫名奇妙的明星﹐集中地反映某些女性感情的幻滅﹐《風信子》寫宋家﹐野心大﹐奈何虎頭蛇尾﹐人物性格模糊佈局雖巧亦無補於事。《兩個女人》是最平淡不可觀的劣作;《胭脂》大而無當;《曾經深愛過》瑕瑜互見﹐但結局乏力﹐有點不知所云。
中篇以《星之碎片》、《蝎子號》、《南星客》及《曼陀羅》及《珍珠》為代表。《星之碎片》及一系列有關丹薇的故事﹐往往和台灣的生活有關﹐有種彷徨失落﹐是亦舒小說人物最低落的一個階段。《蝎子號》勝在自然﹐當然﹐這裡有高達《阿爾伐城》的陰影﹐但就文字而言﹐是亦舒後期文體的濫觴。《南星客》輕巧可人﹐是《蝎子號》的變奏。《曼陀羅》寫慕容寧馨兒——單單這名字已應拍案叫絕﹐絕色佳人情亦絕﹐真是恰到好處﹐不多不少。《珍珠》將心理分析及情意結胡扯一番﹐實在說不過去﹐但全篇的黯澹氛圍﹐她的mood可謂別具一格。
《藍這個顏色》收了《黑色笑話》﹐是她自嘲味道最濃的中篇﹐有點夫子自道的反諷﹐尖刻有餘﹐味道不味﹐不及她同期在「明周」寫的《母與女》。《母與女》的完結篇是她近年最自然感人的片段。
且話亦舒短篇小說﹐讀她的短篇﹐實在是考驗自己的記性:同一集中作品﹐看到第四篇便忘了第一篇﹐看了第三部便忘了前兩部﹐但讀到「新作」﹐便有眼熟之感﹐好像在那裏見過。結果讀了二十四部小說集﹐人物都忘得乾淨﹐只餘十多個書名。
亦舒改書名功夫一流﹐將《紅樓夢》、宋詞、雋語俗語﹐——入題﹐如《花事了》、《囘南天》、《今夜星光燦爛》、《暮》、《過客》、《今夜不》﹐縱使與書中人相忘﹐也還忘不了這些名字。
短篇小說其實極難寫﹐只要有一處敗筆﹐全篇盡廢﹐不似長中篇有挽回的餘地。亦舒寫的短篇﹐當不下五百篇﹐好的實在不多﹐數十篇屬中規中矩﹐好的只有十多篇。
《家明與玫瑰》是較稚拙之作品集﹐無甚可觀;《寶貝》集中的〈信〉有點像張愛玲的《花凋》﹐但文筆生硬;〈寶貝〉是《喜寶》的變奏﹐不過味道差多了;《藍鳥記》中有關婚外情的篇章﹐有可讀之句﹐像「造愛像擦牙」之類﹐《囘藍天》及《今夜星光燦爛》名字好﹐文字平平;《遇遇》、《舊歡如夢》、《花事了》都缺乏新意﹐隱約見出亦舒題材有衰歇之象。到《暮》、《過客》及《戲》才有點新意﹐文字更純淨。

如果拿亦舒短篇的意象來談﹐一定被譏為小題大做﹐但好的短篇﹐意象一定出眾﹐《過客》中的〈電話〉是代表﹐內容不過一男一女藉電話而產生感情﹐但文字佈局不落俗套﹐如篇中寫:
『廚房應有盡有﹐我燒開水﹐做茶﹐打開冰箱﹐拿出石榴﹐切作兩半﹐坐在客廳中﹐一粒一粒剝出來吃。
石榴對我來說﹐是神秘而美艷的。你看過希臘神話嗎﹐有沒有聽過大地之母的故事?她有一個獨女叫寶賽翩﹐一日春遊﹐寶賽翩給冥王普路圖瞧見﹐冥王把她強搶到地獄﹐要立她爲后。地母震怒﹐使大地五穀不生。天神宙斯令普路圖釋放寶賽翩﹐地母下去接女兒﹐囑女兒什麽也不可吃。但是寶賽翩經不起冥王苦勸﹐吃了三粒石榴子﹐從此以後做了冥后﹐一年之內只獲得六個月回到地上﹐因此大地只有春夏兩季﹐有植物生長。
石榴子。
我把子吐在水晶灰缸中﹐這間房子什麽都有。租金並不便宜。原來我想在《茱麗亞》那種近海灘的房子﹐但是收入可恥﹐租不起﹐所以只好租這一層公寓﹐我覺得也很過得去。
整個下午我花在整理衣服上。把裙子一件件掛起來﹐把毛衣摺好﹐藏好璋腦。
覺得累已是下午四五點﹐太陽下山﹐把窗外的影樹頂的火紅。
我倒下床。
床是那種有銅柱的﹐被單床褥全套見全﹐租這套公寓跟租別的不同﹐這像是在外國﹐房東把一切都準備妥當﹐當我醒來時﹐電話鈴已響了很久。我只需要躺下來睡。
叮鈴鈴﹐叮鈴鈴。
我看錶。我腕上戴著一隻十八K金勞力士蠔式表﹐永遠不脫下來﹐洗澡游泳都帶著它﹐時間是十一點一刻。
我本來不想接電話。夜了。我並沒有親友。
但是電話在客廳中不往清脆地響。
叮鈴鈴﹐叮鈴鈴。
十分的遍切與渴望。
終於我赤腳走出去。
拿起話筒﹐我「喂?」
「哦﹐吵醒了你。」一個男人的聲音。』
這是她文字的本色:清淡、乾淨﹐言之有「物」——物質享受的根本意義﹐斷句清晰﹐節奏自然﹐文字要寫到這樣不容易﹐也不是讀讀《紅樓夢》、《水滸傳》、《小王子》或魯迅便可倖致﹐它是不斷創作求進十多年的成果。篇中從石榴子到家明的聲音﹐對影樹的印象﹐都很流暢。篇中警句:
「我喜歡他的聲音。」
對梅麗斯來說﹐喜歡他的聲音﹐也就是愛了——愛使她甘於一等再等。
亦舒結集短篇小說有一特點:喜歡將發表時序不同的作品混為一集﹐所以﹐文字水準不定﹐台灣時期就較近期的鬱結。但《璧人》、《可人兒》、《白夜女郎》、《傳奇》、及《今夜不》都已將觸角伸遠了些﹐《杜鵑花日子》里的〈米雪兒〉就是少數動人的短篇﹐有點自傳的味道。至如較近期的《不要放棄春天》、《哀綠綺思》、《蝴蝶吻》﹐都有老調重彈之弊﹐惟文字保持水準。《阿細之戀》有些像舊作重編﹐未看完已忘了一大半﹐看完便全忘掉﹐一字不留。

要了解亦舒?讀齊她十多部散文集可能是捷徑——從她中四投稿時六元千字的往事﹐到她在報紙寫「墮落」﹐應有盡有﹐更有說不完的《紅樓夢》、《兒童樂園》﹐喬哀思精品店、詩韻、方盈、張愛玲、西西﹐父母兄弟及稿費。
當亦舒寫「讀者讀者我愛你」時。作為老讀者﹐我只好歎聲:「開到荼蘼花事了」﹐對她的作品可謂倦怠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