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isma: Jacques Brel —— 黎海寧 1981 年 6 月 號 外

三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在一間的士夠格裡跳舞﹐忘記了為些什麼打了個電話給鄧小宇﹐講完要講的事情後﹐他告訴我﹕「你知道嗎﹖Jacques Brel 已經去世了。」
我當時的感覺很奇怪﹐在這樣一個人聲鼎沸的場合﹐在電話中﹐聽到一個死訊﹐而這個令我深深震動的死訊﹐對那些當時在我週圍、和我一道跳舞的人﹐是全無意義的,我無法向他們解釋我心情上的突然轉變﹐也並不打算這樣做。再想一想﹐朋友之中﹐還有那一個會對這個死訊作出一點反應呢﹖也還只有 Amy 吧﹐再數不出其他了。翌日﹐我到報攤買了一份《Newsweek》—— 小宇消息的來源﹐然後再去找那份據說用了 Brel 作封面﹐以很大篇幅報導他葬禮情況的《Paris Match》﹐但很可惜﹐我一直都找不到。

十多年前﹐Brel 原是我和 Amy 之間的一個秘密。那時我不與任何其他人談起 Brel﹐因為我直覺地認為他的音樂只可能引起兩種反應﹕一是絕對的著迷、一是絕對的抗拒﹐而我是絕對不能忍受別人﹐特別是自己的朋友﹐對他的拒絕。與其讓他暴露在別人面前的挑剔、選擇﹐倒不如盡量避免公諸於世。而另一方面﹐我那時其實一直在隱約地懷疑自己的口味﹐試想要是有人問我﹕你怎麼會喜歡上一種如此大聲疾呼、感情澎湃、多愁善感的音樂﹖我該如何作答﹖我有沒有足夠的理由及勇氣去為自己及為 Brel 辯護﹖那時我正處於一個較軟弱的年紀。因此﹐有朋友來訪時﹐我永遠不會在唱盤上放上一張 Brel 的唱片﹐而且很奇怪﹐這麼多年來﹐我亦從來沒有見過誰在家裡播放 Brel 的歌。Brel 這個話題從來沒有被觸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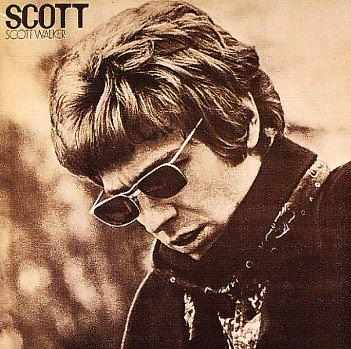
Amy 與我是在一種很奇怪的情況下開始聽 Brel 的。大約沒有多少人會記得﹐英國曾經有一隊名為 Walker Brothers 的流行樂隊﹐瘋魔一時﹐歌手 Scott Engel (即Scott Walker) 更是最突出的人物﹐他憑著一頭捲曲的金髮、英俊的面貌與及刻意營造的憂鬱孤獨形象﹐成為無數女孩子的偶像。那時 Amy 與我瘋狂搜購他的照片及資料﹐每一期的《Rave Magazine》都買回來﹐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有沒有他的消息。有一天﹐Scott 在一篇訪問裡說﹐他最崇拜的人物就是 Jean-Paul Sartre 及 Jacques Brel。我們最崇拜的人所最崇拜的人 —— 這還得了﹖於是立刻展開熱烈的討論﹐又趕忙去買這個叫做 Sartre 的著作來看﹐但是 Brel —— 沒有辦法﹐找不到他的唱片﹐簡直就沒有人知道他是何方神聖。
沒多久﹐Walker Brothers 就拆夥了﹐跟著 Scott 就出版了他第一張個人大碟﹐裡面赫然有著〈Mathilde〉, 〈My Death〉及〈Amsterdam〉三首 Brel 的作品。自此﹐我便一直沉迷在 Brel 的世界裡﹐不能自拔。至於 Scott Engel﹐再出了三四張唱片﹐再為我介紹多幾首 Brel 的歌曲如〈Jacky〉﹐〈Next〉之後﹐就逐漸從樂壇上銷聲匿跡。我也不知從何時起把他淡忘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不假思索地接受了 Brel﹐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我的偶像 Scott 之大力推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種少年的虛榮心所使然。那時候對什麼東西都是很努力地想去明白的﹐越是自己未經歷過的事物﹐未體會過的心情﹐就越是努力地去在想像中經歷、體會﹐跟著就真的以為自己明白﹐比起同齡的朋友更加懂得愁滋味了。其實〈Mathilde〉、〈My Death〉不錯是情歌﹐但那是怎樣的一種情歌啊﹐是那種咬牙切齒的、自虐的、把痛苦和快感都混在一起﹐毫無羞恥的情歌。我那時又怎懂得這些、怎能懂得〈Amsterdam〉的寥寂惆悵﹐〈Next〉的慘痛無奈﹐或是〈Jacky〉的嘻笑怒罵﹖正如我那時剛開始看 Dostoevsky﹐根本就無往理解 Prince Myshkin 與 Nstasya 之間那種曖昧而又激烈的感情﹐但還是要裝著看得律津有味。聽 Brel 的歌﹐最初也是同樣的情形﹐先是被各種奇特的感情狀態所震驚﹐迷惑﹐然後要裝成毫不在意﹐司空見慣的樣子。理解的過程是在接受了之後才緩緩展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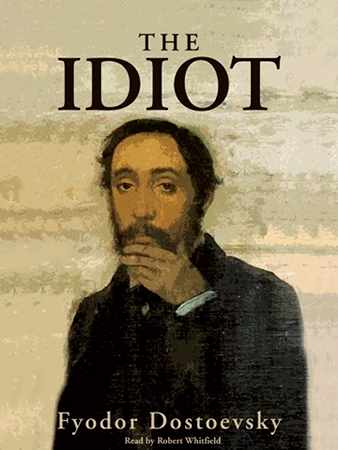
可是﹐Scott Engel 的英譯版本是不足夠的﹐我們都急不及待地要聽 Brel 自己的聲音。於是有一天﹐Amy 帶回來她第一張 Brel 的唱片﹐其中有〈Ne Me Quitte Pas〉(If You Go Away)﹐〈Marieke〉﹐〈La Valse a Mille Temps〉﹐及〈Quand On N'a Que L'amour〉。當〈Ne Me Quitte Pas〉那空靈的泛音小提琴前奏第一聲響起時﹐我就立刻知道﹐我以後再不會相信任何其他人對 Brel 歌曲的演繹﹐包括 Scott Engel 的在內。這之前或之後﹐每一個唱〈Ne Me Quitte Pas〉的人﹐都只是把這首歌作為籍口﹐不是在盡量地表現自己音域之廣闊﹐就是在無限地誇張自己感情之充沛﹐那效果就像是把一首詩變成了一個通俗劇。你可以想像﹐當我後來在電視上看到筷子姊妹花用一口死記的法文﹐或是亞洲歌后聲淚俱下﹐跪在地上唱〈Ne Me Quitte Pas〉的時候﹐我是多麼的難過、氣憤﹐而又無處申訴。還有一個人﹐拿著 Brel 的〈Le Moribond〉改編成〈Season in the Sun〉﹐糟塌得不成樣子﹐我在這裡簡直不願意提他的名字。
在香港要收集 Brel 的唱片﹐是一件頗為困難的事。兩張45轉之後﹐我第一次買到 Brel 的大碟﹐是《Brel' 67》。很久很久之後﹐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一年﹐Brel 公開宣佈從此告別樂壇﹐轉向影壇發展。而我還如此無知﹐在好多年當中不斷希望能一睹他演唱的風釆﹗也幸好他並沒有完全遵守退休的諾言﹐《BREL' 67》之後﹐﹐我還是買到了他兩張唱片﹐其中一張是他在逝世前一年灌錄的。一直到最近﹐也就是他去世後﹐我才在唱片店裡找到了兩套共十多張的Jacques Brel 唱片集﹐包括了他很多早期的歌曲﹐使我終於能較全面地認識他的音樂。

除了他的音樂﹐我對 Brel 這個人知道得實在太少了。我只知道他是比利時人﹐廿多歲時忽然拋下了妻子、兒女﹐以及家庭為他安排好的事業﹐離家出走﹐之後在法國成名﹐宣佈退出樂壇後演過戲﹐也導演過兩套電影。一九七六年﹐當他巳經知道自己患上絕症時﹐Brel 去了南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居住。兩年後四十九歲在巴黎近郊的一間醫院去世。我從來沒有積極地去找尋有關他的資料﹕在香港是沒這可能﹐在法國時卻很奇怪地沒有感到有這個需要。他的音樂已經是一個太豐富、太耐人尋味的世界﹐充滿千奇百怪的人們 —— 潦倒的、自嘲的、歡愉的、可笑的、狂喜的、絕望的;流浪漢、水手、士兵、醉漢、中產階級、老人、情侶。有時候﹐當我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漫步之際﹐我突然間會感到自己正在走進 Brel 的世界﹕在某些黑暗的角落、某種陽光之下﹐或在一個陌生面孔的眼神裡﹐我會覺得覓到一霎那的線索,Brel 所唱過的街道和人物已疊印在真實之上了。
Brel 在國際樂壇上的名氣﹐不如 Edith Piaf﹐更不如 Charles Aznavour。雖然我很喜歡 Piaf 唱的一些歌﹐但是我總覺得她無論唱快歌慢歌、是喜是悲﹐用的都是同一種淒啞的腔調﹐永遠也不能脫離她那種街頭賣唱小婦人的味道﹐聽得多也就覺得厭倦了﹐而且 Piaf 唱的歌地方色彩甚濃﹐很難吸引那些對典型法國 chanson 根本不感興趣的人。與她相比﹐Brel 的歌曲在結構上和配樂上就更多樣化﹐不同性質的歌有不同的處理﹐有些歌是絕對城市的﹐有些卻甚具田園味,有些十分 music-hall﹐有些卻具有古典歌曲的格局,唱得婉轉、激昂或嘲諷時是幾種截然不同的性格。
至於 Aznavour﹐他的情歌的確經常叫人感動不已﹐可是數年前我在 Albert Hall 看過他一次演唱﹐卻大為失望﹐偌大的音樂廳好像完全把他吞沒了。他在台上有時竟然不能提供一個視線的集中點﹐他低調細訴式的演唱在唱片上能令人回味無窮﹐但在這裡卻完全起不了作用。可能一個較 intimate 的環境﹐如一個小小的酒吧﹐更適宜 Aznavour 的規範及風格。我沒有看過 Brel 在台上演唱﹐但不難想像﹐他歌曲裡那種氣勢﹐是絕對可以征服空間的﹐而難得的是﹐他細膩之處卻又直迫 Aznavour。
Aznavour 的歌也是法國的﹐再加點美國爵士樂的影響﹐而 Brel 的範圍是歐陸的﹐美國成份也較少。雖然他可以千變萬化﹐但亦不乏一貫的風格。他的歌曲很多時是慢慢地 build up﹐到了某一點就爆發出來﹐很適合他那些戲劇性的題材。如〈Ces Gens-la〉、〈Fils de ……〉﹐〈Mon Enfrance〉等等都是這樣。每逢我聽到這些高潮的段落﹐我就覺得 Brel 在此時簡直巳經到達了人類感情的頂點。也許很多人對 Brel 可能會有的批評﹐就是他太多了、太強了﹐但我卻認為多的及強的也可以是不粗糙的、不虛張聲勢的。除了激情﹐他還有一份苦澀的幽默感及一種醇厚的溫柔﹐前者需要一段時間去接受﹐後者的魅力卻是顯而易見的。他最感動的歌聲都是寫對逝去或離去的友人和愛人的懷念﹐如〈Fernand〉﹐如〈Jojo〉﹐如〈Marieke〉﹐又或者像〈Jef〉寫出那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像〈L'osten-Daise〉及〈L'eclusier〉寫落寞的情懷﹐都是絕望中滲進溫柔。也許他最後灌錄的大碟裡的一首歌〈Voir Un Ami Pleurer〉最深刻地表達了這種情感﹕當一切都不再美好﹐一切都令人失望﹐但當看見一位明友流淚時 ……。

對我來說﹐Jacques Brel 的死並不像很多其他偶像的幻滅一樣﹐標記著成長過程中某個階段的完結。相反地﹐在我對很多事物的反應都趨於麻木的關頭﹐它重重地刺激了我一下﹐幫我喚起了許多回憶、夢想。我對 Brel 的執著﹐像一條線﹐串起了我所經歷的各個階段。自然﹐我動搖過﹐當 Amy 離我越來越遠﹐當 Brel 逐漸成為只是她欣賞的眾多歌手之一﹐對她再沒有任何特殊意義之時﹐而我還是在如此全神貫注﹐正襟危坐地聆聽 Brel﹐我便開始覺得自己 heavy 得難以忍受了。但後來有一天﹐我接受了自己。而現在﹐光是想到我能持續地喜歡一個人達十幾年之久﹐就足以使我對自己恢復信心;再想起 Brel 的歌﹐我便覺得﹐也許人是不一定要那麼講究瀟灑的。
正當我以為我這一生也沒有機會能看到 Brel 演唱的神態時﹐電視上竟然放映了《Jacques Brel is Alive and Well and Living in Paris》這套根據舞台劇拍成的電影。其中 Brel 竟然出現﹐並且唱了〈Ne Me Quitte Pas〉!如意料之中 (因為他歌曲的意境是沒有可能用別的方法由別人去表達的) 這套電影差得可以﹐四\個小丑般的人物﹐毫無說服力地唱了 Brel 的很多首歌。導演出盡法寶﹐為每一首歌安排了不同的處境﹐動用很多配角﹐加插很多活動。可是這一切道具﹐一切佈景﹐一切活動﹐加起來都不及 Brel 獨自一人坐在那裡﹐默默地冷眼旁觀﹐又或者是依舊坐在那裡﹐不用任何襯托﹐不用一個手勢﹐靜靜地﹐如同整個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似的﹐唱完一首歌。在這一刻裡﹐我忽然覺得自己十分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