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年輕狂妄時的金句 2018年7月 立場新聞

今個星期一直記掛住書展十九號那個六十年代依達和亦舒的講座,也要做些功課,才發覺網上這兩位作者生平資料原來少之又少,然後醒起亦舒曾在1977至1980年間替《號外》不定期寫文,我找到的共十五篇,一早已珍而重之上傳到我的網站,今次翻來看看可以找到些什麼漏網材料,居然給搜索到一些她無意中透露的個人資料。
重讀這些舊文依然津津有味,既精闢又十分亦舒,直頭是妙不可言,反正我腦袋暫時已轉不返來現實,不如就輯錄當中一些她年輕狂妄時的金句分享:
【談小電影 (A片)】
我對上班也沒有與趣﹐還不是天天早上七點半起床往辦公室前進﹐做人有時候不能免俗﹐故此絕少在播放小電影期間站立離場。數衍數衍﹐也就坐到完場。
我絕不會發動看小電影﹐正等於我不會發動到避風塘去吃東風螺﹐純是興趣問題﹐與道德水準及審美觀念無關。
【談性】
香港再現代化﹐也還是老土的香港﹐女孩子出嫁之前的青春﹐一定要在家中「虛渡」若干春天﹐碰到對象﹐在戲院公園馬路﹐甚至十四座位小巴中廝磨一番﹐然後正式嫁到夫家為家庭「犧牲」﹐努力在腰圍上添增士啤呔﹐註冊結婚那一日﹐還要討價還價的逼新郎在門外討開門利是﹐俗得啞心﹐虛偽得肉酸﹐其荒謬之處﹐伊昂尼斯高的劇本甘拜下風。
浸豬籠的時代已經過去﹐但是中國人對性的觀點還是那麼奇怪﹐孩子不停的被生下來﹐咀裏不准提到那回事。民族性比誰都黃且好色﹐放著玉蒲團、金瓶梅、素女經不觀之鑽之研之﹐專門托人在北歐帶小電影回來欣賞。(我)在辦公室裏看「花花公子」訪問卜狄倫﹐尚有同事嘩聲四起﹐中國人不但一切有假面具﹐在這方面都不放過﹐放屁都要先假道學一番﹐
【談粗口】
十餘年前女人開口說粗話﹐有震壓力﹐說粗口也是藝術﹐亦有潮流﹐現時這潮流已經過去﹐像吸煙﹐除非真有需要﹐否則女人當眾夾枝香煙﹐到底難看相﹐不信照照鏡子。也等於服鎮靜劑 …… 都開到荼糜花事了 —— 難道大家不見得俗﹖等於花生漫畫與小王子故事﹐別再提了﹐拜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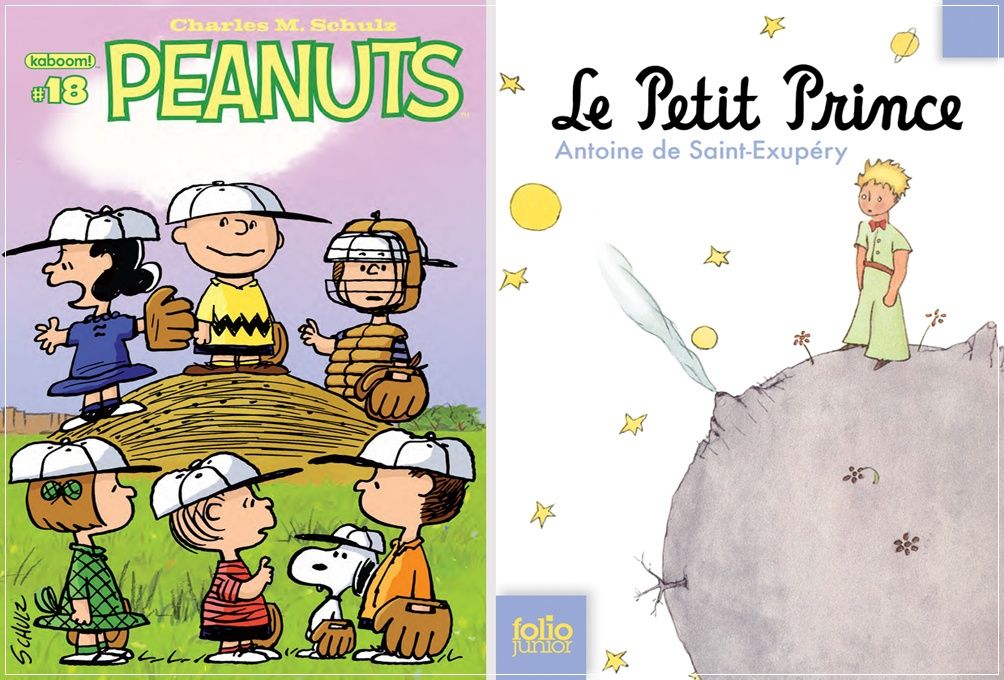
林青霞可以肯定是不說任何髒言的﹐但當年的李菁與何莉莉卻是其中好手。男人其實很怕女人潑。有一日莉莉穿件低胸衣裳晃來晃去﹐羅烈上前故意偷偷地張望又張望﹐莉莉忍不住把衣服拉開:「看﹗看你的媽﹗」從此羅烈叫她「媽」。
我認為這一類髒話非常幽默可喜﹐無傷大雅﹐且富時代感。我喜歡莉莉﹐泰半是為著這種直爽自然。簡而清說:「在適當的地點﹐與適當的人﹐說幾句適當的粗話﹐實在有震撼感。」這是可以相信的。
【談購物】
香港人喜歡購物﹐從巴黎買到馬尼拉﹐總有辦法一蘿筐一籮筐的東西抬回來。
香港大部份女性穿衣服是極徬徨的﹐並沒有主見﹐且花不起錢﹐又怕瞧上去老土﹐常常無所適從﹐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停止。
買或不買﹐這是問題。
困難是自幼只穿純棉純麻純羊毛。但世上沒有絕對的事。自幼是自幼﹐現在是現在。現在到什麼地方去找這麼便宜的衣服。於是速戰速決﹐廿分鐘內選妥五套。
我的理想基在詩韻時裝有限公司 (甚至不是喬哀斯店) ﹐在那裏﹐一切生活上工作上的怨鬱委曲﹐一下子就申訴乾淨﹐我知道該往那裏去﹐開步到女裝部去。(那篇文標題是「中國往哪裏去」)
十七八歲的時候走進「鈕蝶屋」簡直再也走不出來﹐最好搭張床睡在那裏。
有一件粉紅色的 Cacharel襯衫自七三年到現在還在穿﹐每次都擱在洗衣機裏狂洗﹐ Cacharel 襯衫 J.B.Martin 鞋子一樣﹐終於壽終正寢的時候﹐不應該把它們扔掉﹐應該把它們下葬。
【談教育】
從前的港大生尚有一種白象式的氣質﹐現時我在街上結識的港大生﹐在席上「啜啜」有聲地㗳著魚骨與雞腳﹐我說﹕「請你住聲好不好﹖」他﹕「這是我的享受。」我﹕「你不能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他愕然﹕「你痛苦嗎﹖」我﹕「非常﹗」
怎麼叫做英文好呢﹖有什麼標準呢﹖陶敏明說狄龍的英文巳經夠好了﹐因此狄龍不需要再學。
我老覺得目前香港遍地黃金﹐根本不需花很多勁去揀﹐一個人需要很大的定力﹐才能堅持唯有讀書高﹐然而知識是一切廉恥感的泉源﹐讀書人最大的痛苦是許多事做不出來﹐錯過太多。
香港的教育不過包一個青年人獲得一般知識﹐通過考試﹐假如他懂得做人﹐在機關中平步青雲不是難事﹐如果他喜歡﹐也可以追電視台小明星或是香港小姐。文化是叫子女去學鋼琴 …… 至於宋徽宗是否姓宋﹐interview 中不考這一條。
或者這樣的鄙視香港教育是不應當的。每當〈天佑女皇〉一響起﹐我就告訴自己﹕不愛聽﹖願否回大陸﹐或是到台灣﹖然後我就霍然起立﹐我們毫無選擇﹐不止是教育問題。
【談自己】
我個人反對生命﹐覺得生命是無謂的浪費﹐整個過程是無限量的痛苦﹐孩子們是最無辜的受害者﹐因此一向贊成墮胎合法化。
天地良心﹐我寫的小說比我寫的散文更精彩﹐也更富自娛性。我是我的小說裏面的人物的上帝。在我的小說中﹐愛情都沒有結果﹐因為男女主角總是巧合地相遇在不合適的時間﹐不合適的空間和不合適的身份裏﹐倘若給他們委曲求全了﹐到底意難平﹐反不如無休止地等待吧﹐天見可憐。況且我不信任婚姻。故此我筆底下的王家明是永遠得不到玫瑰、明珠或者周丹薇的。這是人生。
我的身份證上清清楚楚註明我是中國人。但老老實實﹐對於中國人的生活細節﹐我一向不甚了了﹐正等於友人們堅持我不吃「飯」沒營養 —— 牛奶雞蛋加燒牛肉三文治加蘋果是沒營養﹐他們蒸一碟子鹹魚﹐炒一盆蓊菜是有營養。我不明白。
恐怕不明白也沒有關係的﹐至少香港已經進化得容許我這種人的存在。至於我﹐闖了這麼多年﹐獨力打天下﹐現在畢竟累了﹐由心底每一個細胞累出來。自己看看﹐房間裏面每一樣東西﹐連一粒釘 (還有那張美過美麗的書桌)﹐也是我自己買的。可是﹐這又有什麼快樂可言呢﹖所以﹐假如讓我碰上了一位年輕、富有、英俊而帶點邪氣的物理學博士的話﹐我會毫不猶疑的下嫁於他﹐祇要他要我。說句坦白話﹐我急於脫離金寶罐頭湯的日子。
我想接受教育是終身大事。自學校開始﹐不過是基礎﹐下了種子一直長﹐至死時停止。
上一篇:2018 姚松炎形象的致命一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