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肯定好東西 —— 陳冠中 1994 年 5 月 號 外

總經理麥成輝和總編輯趙德強叫我快點寫文章給這期《號外》,到底是跟張愛玲同期出現,機會難逢。他們真照顧我。
《號外》十八年來一貫擁張,她帶給了我們重大的啟發、教育、姿勢、文字、激情,我們借了她的感覺來重認自己:比我們先知先覺的人是有(如夏志清、宋淇和皇冠出版社的平鑫濤),比我們遲鈍的同輩人更多(如大陸官方評論界和台彎一撮鄉土派),現在都不用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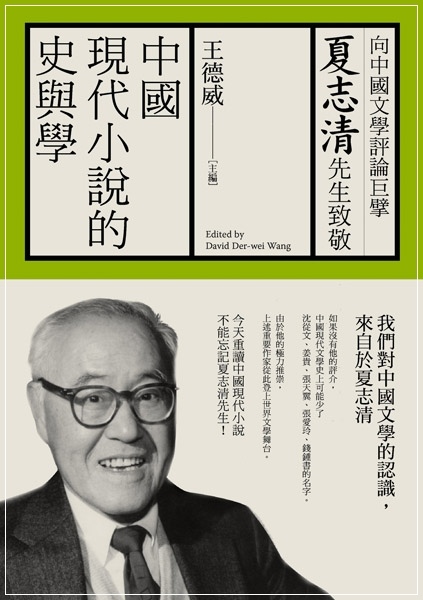
李歐梵在他的新文集《狐貍洞話語》說:「如今大陸學界對五四文學的這種無意義的作家政治排行榜 —— 魯(迅)、巴(金)、茅(盾)、郭(沬若)、老(舍)、曹(禺),已經被人擯棄,反而是未入榜的沈從文、張愛玲、穆時英、施蟄存、師陀等作家陸續得到學術世界的重新肯定。」其他我不知道,張,我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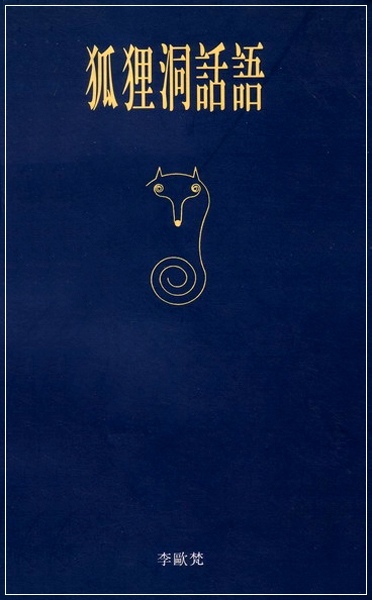
大概腦子已經「大陸化」,所以我才敢對大陸的潮漲潮落說我知道,好像電影《與狼共舞》的白人騎兵,自我放逐在邊域太久,與印地安人同了步。(當然,對北京人來說,香港才是邊域。)
注意的都是大陸問題,就算問題的引子是在海外。好像: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二十一世紀》前陣子發表國家能力論的一組文章,兩位學者王紹光(現在美國)和胡鞍鋼(現在中國)主張加強中央汲取全國資源的能力,並以此能力與國家富強勾掛,在海外是引起了圈子內的回響,在北京則是知識界的話題,可別忘了好一段時期大家的默契是贊同中央向地方分權讓利,甚至把「非中心化」視作擴闊「民間社會」和建立「公眾空間」的條件,現在國家富強之路又向中央集權集利(譬如稅務上是與地方分稅,不是定額上繳)傾斜。
這場爭論方興未艾,正反文章相繼出籠。學術討論隨時可以影響國策,也是中國還是有人願意好好寫學術文章的原因之一吧。

至於白人騎兵,回到自己的營地,就會給其他白人同僚罵他“turned Indian”。我回到香港,看電視劇《清宮氣數錄》,就 —— 不可能這樣糟糕吧。
我們香港人真多集體盲點。
這樣的劇在大陸不可能出現,首先愛新覺羅家族和滿人會抗議,其次,有違我黨我國多民族共存原則。對大漢中心主義,大陸比香港自覺。(同樣,歐美國家也不敢再作弄少數民族形象,只有香港人才有這樣胡來的自由)。
我不是鼓吹政治正確論,而是說出有點尊嚴的作品來。
對滿清一朝,對康熙、雍正、乾隆、慈禧,多少的好書,在香港人的故事性想像力中從未存在。但至少,我們不應從《書劍恩仇錄》的水平倒退呀!
至於對洋人的典型想像,好像永遠是簡化至(想像中的)霍元甲打倒俄國大力士、李小龍打鬼佬、中國人不是東亞病夫 —— 這個層面。香港鄉紳,我在說你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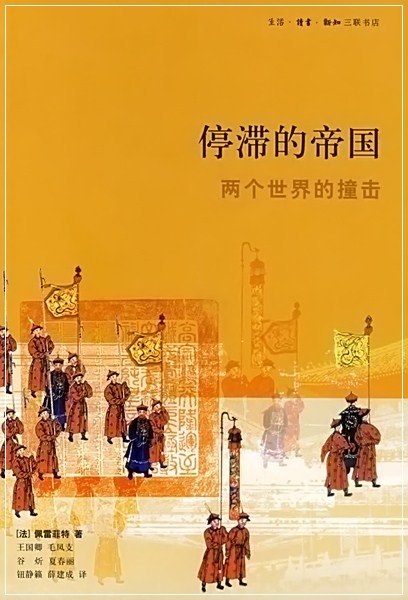
對香港「說故事人」來說,佩雷菲特 (Peyrefitt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這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已經出版的書是等於沒有出版。香港說故事人與外間世界不是「聾子的對話」,而是自我的交配 —— bad TV begets worse TV。
所以你說,前陣子北京引進薩依的東方主義一說,能不叫人驚心動魄!一個不小心,會變了把歷代的西方學術一筆勾銷。還是先醫好我們自己的西方主義(即用中國角度判斷西方)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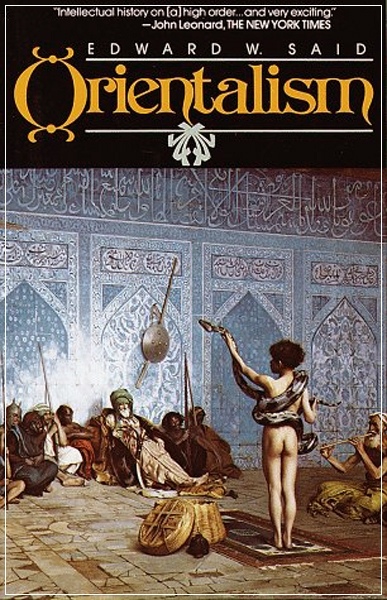
李慎之好嘢。
推介: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中國六百年農村發展的實證研究來動搖一些概念先行的理論,包括我輩急進年代談的資本主義萌芽論對封建論,和學習(西方)社會科學時談的傳統與現代命題。黃的書應可不受東方主義或西方主義的咎病了。
不同文化的溝通真難。梁濃剛,你還在寫東西旅遊文化的交流史嗎?
敬愛的張愛玲,你還在揣摩大洋人類學嗎?
最後,讓我賣點藥:我剛在北京跟三聯簽了約,七月在香港發行《讀書》月刊的繁體字版。
讓我們肯定好東西。
上一篇:1989 沒有品牌的香港
下一篇:1995 寫在號外十九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