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 1976 年 12 月 號 外

最近想寫 Stephen Sondheim﹐便問友人借了 Judy Collins 的近期大碟《Judith》﹐聽聽她怎樣去處理 Sondheim﹐卻無意中被裏面另一首歌吸引住。真的﹐我很久沒有聽過一首如此令人難過的歌曲﹐Collins 一向的缺點是過於平淡﹐但這次她卻平淡得恰到好處﹐並沒有誇張歌中的辛酸﹐用 bossa nova 節拍伴奏的幾個結他也沒有去強調那本身已經很淒涼的調子﹐我甚至當初沒有留意歌詞說些甚麼﹐只是一接觸這首歌﹐直覺上就感到很沉重、難受﹐那種感覺很自然令我想起小時候看完冰心的短文「到青龍橋去」時的心情一樣 —— 大家都是默默地去忍受世間上的不公平。

後來我問胡君毅﹐才知進那是三十年代美國經濟大衰退時一部音樂劇 Americana 裏面的插曲。 Peter Yarrow (Peter, Paul & Mary 的 Peter) 也曾在 "See What Tomorrow Brings" 那張碟裏面獨唱過﹐聽說成績也十分精釆﹐所以如果你像我很多朋友一樣﹐真的不能忍受 Judy Collins 的話﹐就記緊找 Yarrow 的版本來聽聽。
對了﹐忘記告訴你﹐那首歌叫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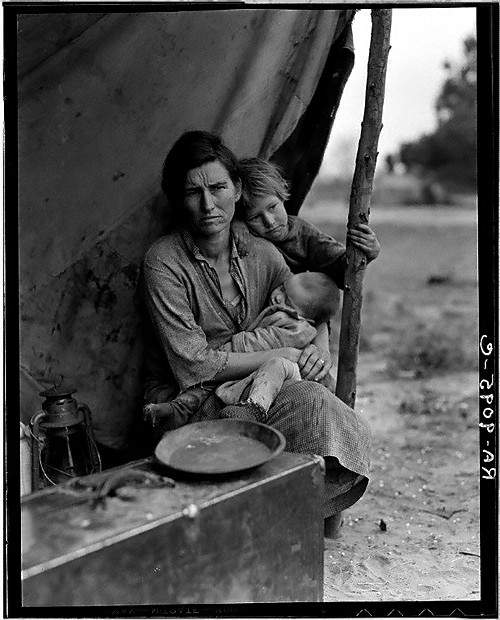
到青龍橋去 —— 冰 心

如火如荼的國慶日,卻遠遠的避開北京城,到青龍橋去。
車慢慢的開動了,只是無際的蒼黃色的平野,和連接不斷的天末的遠山。 ——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風般從車前飛過。不時有很淺的濃綠色的山泉,在岩下流著。
山半柿樹的葉子,經了秋風,已經零落了,只剩有幾個青色半熟的柿子掛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著晨風,一片的和山偃動,如同一領極大的毛氈一般。
“原也是很偉秀的,然而江南……”我無聊的倚著空冷的鐵爐站著。
她們都聚在窗口談笑,我眼光穿過她們的肩上,凝望著那邊角里坐著的幾個軍人。
“軍人!”也許潛藏在我的天性中罷,我在人群中常常不自覺的注意軍人。
世人呵!饒恕我!我的閱歷太淺薄了,真是太淺薄了!我的閱歷這樣的告訴我,我也只能這樣忠誠而勇敢的告訴世人,說:“我有生以來,未曾看見過像我在書報上所看的,那種獸性的,沉淪的,罪惡的軍人!”
也許閱歷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卻不敢欺哄世人!
一個朋友和我說,——那時我們正在院裡,遠遠的看我們軍人的同學盤槓子— —“我每逢看見灰黃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種憎嫌和恐怖的戰栗。”我看著她鄭重的說:“我從來不這樣想,我看見他們,永遠起一種莊肅的思想!”她笑道: “你未曾經過兵禍罷!”我說:“你呢?”她道:“我也沒有,不過我常常從書報上,看見關於惡虐的兵士們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數年來潛在的隱伏著不能言說的憐憫和抑屈!文學家呵!
怎麼呈現在你們筆底的佩刀荷槍的人,竟盡是這樣的瘋狂而殘忍?平民的血淚流出來了,軍人的血淚,卻灑向何處?
筆尖下抹殺了所有的軍人,將混沌的,一團黑暗暴虐的群眾,銘刻在人們心裡。從此嚴肅的軍衣,成了赤血的標幟;忠誠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隨從。可憐的軍人,從此在人們心天中,沒有光明之日了!

雖然閱歷決然毅然的這般告訴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學家所寫的是真確的。軍人的群眾也和別的群眾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壞人。然而造成人們對於全體的灰色黃色衣服的人,那樣無緣故無條件,概括的厭惡,文學家,無論如何,你們不得辭其咎!
也講一講人道罷!將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從教育的田地上奪出來,關閉在黑暗惡虐的勢力範圍裡,叫他們不住的吸收冷酷殘忍的習慣,消滅他友愛憐憫的本能。有事的時候,驅他們到殘殺同類的死地上去;無事的時候,叫他穿著破爛的軍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來守更走隊,在悲笳聲中度生活。家裡的信來了:“我們要吃飯!”
回信說:“沒有錢,我們欠餉七個月了!——”可憐的中華民國的青年男子呵!山窮水盡的途上,哪裡是你們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時無限制的升起。無數的觀念奔湊,然而時間只不過一瞬。
車門開了,走進三個穿軍服的人。第一個,頭上是粉紅色的帽箍,穿著深黃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後面兩個略矮一些,只穿著平常的黃色軍服,魚貫的從人叢中,經過我們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幾個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們略不注意的仍舊看著窗外,或相對談笑。我卻靜默的,眼光凝滯的隨著他們。
那邊一個兵丁站起來了。兩塊紅色的領章,圍住瘦長的脖子,顯得他的臉更黑了。臉上微微的有點麻子,中人身材,他站起來,只到那稽查的肩際。
粉紅色帽箍的那個稽查,這時正側面對著我們。我看得真切:圓圓的臉,短短的眉毛,肩膊很寬,細細的一條皮帶,束在腰上,兩手背握著。白絨的手套已經微污了,臂上纏的一塊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寫著“察哈爾總站,軍警稽查… …”以下的字,背著我們看不見了。
他沉聲靜氣的問:“你是哪裡的,要往哪裡去?”那個兵丁筆直的站著,聽問便連忙解開外面軍衣的鈕扣,從裡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和護照來,無言的遞上。 ——也許曾說了幾句話,但聲音很低,我聽不見。稽查凝視著他,說:“好,但是我們公事公辦,就是大總統的片子,也當不了車票呵!而且這護照也只能坐慢車。弟兄!到站等著去罷,只差一點鐘工夫!”
軍人們!饒恕我那時不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個很大的爭鬧,不覺的退後了,更靠近窗戶,好像要躲開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將片子放在自己的袋裡——那個兵丁低頭的站著,微麻的臉上,充滿了徬徨,無主,可憐。側面只看見他很長的睫毛,不住的上下瞬動。
火車仍舊風馳電掣的走著。他至終無言的坐下,呆呆的望著窗外。背後看去,只有那戴著軍帽,剪得很短頭髮的頭,和我們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動搖。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放下心來,卻立時起了一種極異樣的感覺!
到了站了!他無力的站起,提著包兒,往外就走。對面來了一個女人,他側身恭敬的讓過。經過稽查面前,點點頭就下車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個兵丁問答。這個兵丁較老一點,很瘦的臉,眉目間處處顯出困倦無力。
這時卻也很直的站著,聲音很顫動,說:“我是在……陳副官公館裡,他差我到… …去。”
一面也鄭重的呈上一張片子。稽查的臉仍舊緊張著,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見有絲毫情感的表現,他仍舊凝重的說:“我知道現在軍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們留一線之路。
但是一張片子,公事上說不過去。陳副官既是軍事機關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車上的規矩——你也下去罷! ”
老兵丁無言的也下車去了。
稽查轉過身來,那邊兩個很年輕的兵丁,連忙站起,先說:“我們到西苑去。 ”稽查看了護照,笑了笑說:“好,你們也坐慢車罷!看你們的服章,軍界裡可有你們這樣不整齊的?
國家的體面,哪裡去了?車上這許多外國人,你們也不怕他們笑話! ”隨在稽查後面的兩個軍人,微笑的上前,將他們帶著線頭,拖在肩上的兩塊領章扶起。那兩個少年兵丁,慚愧的低頭無語。
稽查開了門,帶著兩個助手,到前面車上去了。
車門很響的關了,我如夢方醒,周身起了一種細微的戰栗。 ——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回想,呀!竟是最深的慚愧與讚美!
一共是七個人:這般凝重,這般溫柔,這樣的服從無抵抗!我不信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前面……登上萬里長城了!亂山中的城頭上,暗淡飄忽的日光下,迎風獨立。四圍充滿了寂寞與荒涼。除了淺黃色一串的駱駝,從深黃色的山腳下,徐徐走過之外,一切都是單調的!看她們頭上白色的絲巾,三三兩兩的,在城上更遠更高處拂拂吹動。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數千年前偉大建築物的長城上,呆呆的站著,竟一毫感慨都沒有起!
只那幾個軍人嚴肅而溫柔的神情,平和而莊重的言語,和他們所不自知的,在人們心中無明不白的厭惡:這些事,都重重的壓在我弱小的靈魂上——受著天風,我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個我沒有!
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夜。
文集《往事》,開明書店1930年1月初版。

冰 心
上一篇:返回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