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宇訪問:“富二代”,走著瞧 (上) —— 許驥 2011 年 錄自《同胞請淡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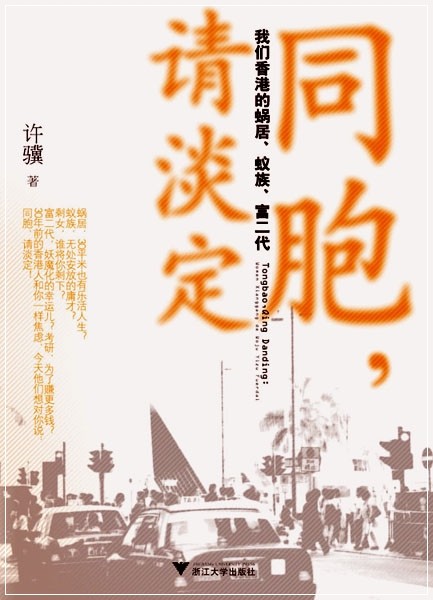
鄧小宇的淡定
香港《蘋果日報》把鄧小宇稱作“品味判官”,說他“是一尾鯨魚,巨大,又溫柔。接近龐然大物時,很多事你都不敢做”。
詩人廖偉棠則把鄧小宇和邁克相提並論,說“那一代香港文化人裡面,最有情調的莫過於邁克和鄧小宇,他們語不涉政治,唯在塵世中來去,文字極豔麗悱惻,造就一幫癡迷者,前者承傳張愛玲,後者曾假錢瑪莉之名書寫時尚,都是富有雙性魅力,當為內地新一代唯美主義讀者深愛”。
而邁克,則用自己的文字讚美鄧小宇的文字說:“鄧小宇永遠不會是鄰家那個模棱兩可的差不多先生,就算在最好相與的時刻,仍然不忘露一露招牌的犬齒。多年前李志超編週刊約寫專欄,揦手唔成勢的我不知道應該寫什麼,他大喝一聲: ‘寫什麼沒關係,我要你的 attitude!’ 我不禁一怔,暗暗納悶:又不是鄧小宇,哪來這麼多現買現賣的 attitude!這個中文通常譯作‘態度’的單詞,加一點海派的鹽花,正是鄧最令我五體投地的特質。”
加入演藝圈的新銳作家王貽興也膜拜鄧小宇的文字說:“這位《號外》創辦人的厲害之處在於他早在 20 世紀 70 年代已經覺醒,把雅皮、感性、品味與自我在那年代優雅瀟灑地向大眾展示,且前衛地把難登大雅之堂的廣東話,配合英文與書面語,造就成為獨特的‘三及第’語言,提升與肯定了廣東方言在寫作上的地位與感染力。”
馬家輝評價鄧小宇的代表作《穿Kenzo的女人》時,簡直用了一種讚美詩的韻味歌唱道: “讀過《穿Kenzo的女人》的我們都心知肚明,這部接近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正可為呂大樂的考察提供最佳佐證:是的,在這部看似以愛情追求為主題卻又遠遠不止於談情說愛的城市小說背後, 其實隱藏著一段波瀾壯闊的香港‘本土文化獨立宣言’。”……
以上,是我零零星星、拉拉雜雜搜集到的香港文化界關於鄧小宇的評論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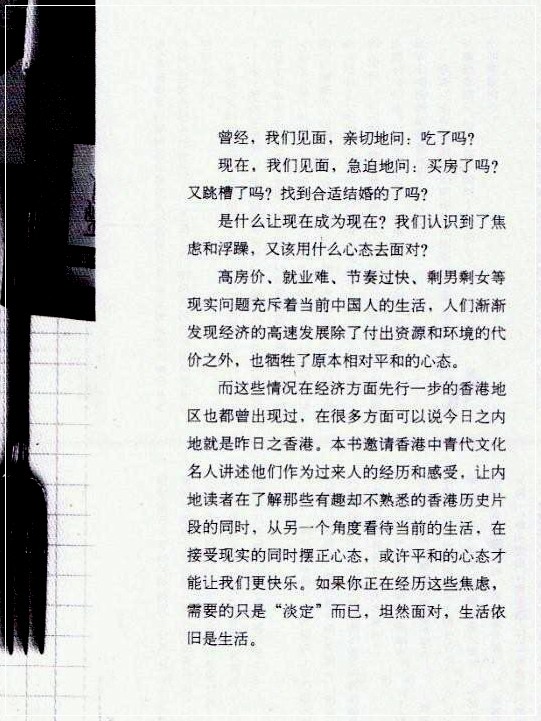
在香港,我想即便你不知道鄧小宇,也一定耳聞過“錢瑪莉”的大名。20 世紀 70 年代末,鄧小宇化身成“拜金女”錢瑪莉,把自己的故事寫成一篇篇精緻的文章,用連載的形式刊登在香港著名的《號外》雜誌上。這些關於女人男人、愛情友情、職場情場的文字,沒想到一經連載,頭尾就是整整七年時間。鄧小宇苦心經營,足足寫了二十萬字,之後結集成為《穿 Kenzo 的女人》(以下簡稱《穿》)一書。這些文字不僅成為馬家輝口中的香港“本土文化獨立宣言”,同時,亦成為對“獅子山時代”的最佳見證。而《穿》之故事編排、結構設置、人物個性乃至語言風格,竟然都與二十年後火爆的美劇《慾望都市》如出一轍。令我不由得心生懷疑——《慾望都市》是否“參考”過《穿》?
只要你讀過《穿》,就知道鄧小宇對有錢人的生活是多麼瞭若指掌。我曾經寫過《穿》的書評《港女拜金,非誠勿擾》(載《南方都市報•閱讀週刊》,2010 年 07 月 04 日),文中,我是這樣概括錢瑪莉的生活的:
錢瑪莉過的是典型的 20 世紀 70 年代香港白領女性生活,被物質充斥得密不透風。所以,這本書裡也到處可見各種名牌的身影。這些白領的腦子裡,每天想的都是如何賺更多錢買更貴的奢侈品,如何嫁更有錢的老公,以此來取得朋友們青睞的目光。小說一開始,錢瑪莉就因為身著 Kenzo 牌衣服,被《號外》雜誌的眾編輯盛讚“有趣”。有人忽得靈感,給她開了個專欄 —— 穿 Kenzo 的女人。從那天起,錢瑪莉就把自己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新歡、舊愛、分手、失戀一覽無餘。身邊雖有無數男人在追求她、供她選擇,錢瑪莉卻在找尋一段“完美” 的婚姻。最令她糾結的是:在愛情與金錢之間,究竟孰輕孰重?怎樣去深入瞭解一個男人,以便確信自己要和他白頭到老?
錢瑪莉是高級白領,收入豐厚,可你千萬不要誤以為她會滿足於現狀。冷靜的時候,她勉勵自己通過努力得到更好的生活;但浮躁的時候,她也會發出這樣的怒吼:“我已經厭倦做一個高級行政人員,我的夢想是一個高級行政人員無法達到的,我需要很多的金錢,唯一的方法就是嫁一個很有錢的丈夫。不要再在我的面前提起那些月入一萬的男人了,和他們結婚是死路一條!”錢瑪莉的話雖然說於二三十年前的香港,可在今天內地社會裡,還是很有共鳴的。

我把《穿》和法國社會學大師鮑德里亞的經典著作《消費社會》聯繫在一起,指出在 20 世紀 70 年代的香港以及現在的中國內地,整個社會都是一種“消費至上主義”。我說:
香港人在經濟騰飛的年代,曾誤被“消費社會”的幻象所迷惑,以為香港的股票會永遠往上漲,香港的樓價會永遠往上昇,以為社會只要爭得 GDP 的最大化,人也可以同時達到幸福的最大化。他們沒有注意到鮑德里亞已經預言:“今後將會有一個世界性的疲勞問題 …… 無法控制的傳染性疲勞,和我們談過的無法控制的暴力一樣,都是豐盛社會的特權,是已經超越了饑餓和傳染性匱乏的,後者仍是那些前工業社會的主要問題。”壓力在成倍成倍地增加,機會在大量大量地減少。一夜之間,金融風暴來了,泡沫破滅了,香港人全都傻眼了 …… 錢瑪莉沒有繼續寫下去。假如她一直寫到 1987 年的香港股災,我想這本書肯定就更好看了。
鄧小宇為什麼會這麼懂有錢人?因為他在幼年時代曾是童星,拍過數套粵語長片。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騰飛尚處於醞釀階段的香港,他就已經開始接觸上流社會了。當大多數人還在步行的時候,他已經坐慣了房車;當所有人還在吃魚蛋粉的時候,他已經吃膩了魚子醬。當然,這些東西都不用他自己埋單,他在戲中的“媽媽”會帶著他四處遊玩。在 2010 年香港書展鄧小宇的作品分享會上,我坐在觀眾席裡,一邊聽他講述兒時當童星時的夢幻經歷,一邊欣賞著動人的舞曲。他說,這首舞曲就是四十多年前他在一次派對上所聽到的。在他的記憶中,扮演他媽媽的女明星好漂亮、好高貴、好風雅,她伴隨著這首音樂翩翩起舞,銀色的月光灑在她身上,性感極了。類似的場景,鄧小宇在另一本書《吃羅宋餐的日子》裡也曾描寫過:“有一晚我父母在沙田華爾登跳舞,見到李湄,‘穿著低胸晚裝,妖豔地、風情地跳恰恰’,他們心中暗叫不妙:這樣一個女人,怎可能演賢妻良母!”
鄧小宇的淡定,是見過了太多有錢人的淡定。他自己或許並不算太有錢,只是經營著家族的物流產業;但是他身邊的人,無論“富一代” 、“富二代”、“富三代”…… 皆有之。《蘋果日報》對他的描述真是精准極了,他確實像一尾鯨魚,巨大而溫柔,“接近龐然大物時,很多事你都不敢做”。一開始,我跟他憤懣地述說“富二代”如何欺壓“窮二代”,憤怒地述說杭州“七十碼”事件發生的經過,憤慨地述說電視劇《奮鬥》完全就是一群“富二代”的荒唐 “創業史”……他聽了,都只作雲淡風輕點頭微笑狀,使我這顆浮躁的心,也都慢慢平靜了下來。
然後,他不疾不徐地跟我講了好多他所見所聞的故事,告訴我,我們今天身邊的富人,基本上都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形成的。“富二代”現在之所以如此張揚,主要是由於“富”的歷史短,一下子還不懂得調節。從香港的經驗看,富人往往是“富不過三代”的。在香港,一百多年來,人們已經目睹太多富人誕生、富人消失的故事,根本不足為怪。馬家輝也曾經跟我講過一個故事,說他認識一個算命先生,年輕時在廟街做流浪漢,最慘的時候窮到用報紙當被子的地步;後來跟人學算命,殺出一條血路,身家最高時有幾個億,半山豪宅區有十幾套單位都是他的財產;但是幾年前莫名其妙就破產了,人也失蹤了。香港多的是這樣的故事,所以頭腦清醒的“富一代”、“富二代”,他們自己心裡都明白得很,既不會過於張揚,也不會誤以為自己家族的富有是“萬古長青”的。
我覺得,一個正常的、合理的社會,就應該是窮人和富人相互流動的,這樣才人人皆有機會。否則,富人永遠是富人,窮人永遠是窮人,整個社會就會呈現一種“板結”的狀態,失去活力、創造力、生命力。當然,我也不是在鼓吹中國傳統的“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思想,這樣一來好像在說社會的總財富是固定的,你佔了我就沒分,我佔了你就休想得到,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實際上,社會的財富應該平穩增加、合理分配,增加出來的部分,應該更多地照顧到窮人。但現實的狀況並不令人滿意,我們所能看到的,是富人愈富、窮人愈窮。尤其是香港這樣的成熟資本主義社會,社會結構僵化得令人窒息,幾乎有“老闆之後永為老闆,店員之後永為店員”的惡兆。
面對這樣的現實:消費至上,社會板結,富人愈富,窮人愈窮 …… 我們還能淡定嗎?

電視劇《Gossip Girl》中的美國富後代
■ “富二代”VS.“二世祖” ■
許:你覺得在香港怎樣能算是“富人”?
鄧: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