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書璇訪問記 (上) —— 陸離 1974 年 1 月 文 林

按﹕「唐書璇訪問記 —— 一九七零」﹐從頭至尾﹐完整刊出﹐這還是第一次。一九七零年十月﹐原文在《中國學生週報》開始刊登﹐之後每隔大約三四個月﹐才繼續刊出二三千字不等﹐結果連載了差不多一年﹐全文支離破碎﹐令人無從卒睹﹐這主要因為筆者自從一九七零年久已不願工作﹐所以後來另外做了兩個訪問﹐一篇請人代寫﹐一篇至今依然拖欠﹐就是這個緣故。其後一九七二年四月﹐第一次退休﹐樂何如之。一九七二年十月﹐為報林以亮先生十年知遇之恩﹐進入《文林》勉勵工作﹐旋於一九七三年一月﹐第二次退休及一九七三年六月複進「文林」﹐至今半載﹐而後決定第三次退休。反復無常﹐有若是者﹐其不適於生存﹐亦殆無矣。僅于此順向讀者告別﹐並祈禱繼續愛護《文林》。
—— 陸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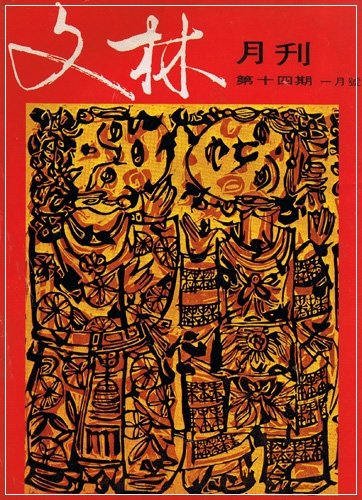
日期﹕一九七零年三月
地點﹕美麗華酒店
訪問﹕顧耳、文世昌、陸離
記錄﹕陸離
攝影﹕沒有人攝影
前言
我們做這個訪問的時候﹐是在三月。由三月到十月﹐七個月以來﹐不能說沒有任何變化﹐關於人﹐關於事﹐但是﹐訪問裡談到《董夫人》的地方那變化應該是不太明顯的。特別是﹐正如唐女士一再的喜歡強調﹐一件藝術品﹐由不同層次的觀眾看來應該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反映﹐因此﹐唐女士本人對《董夫人》某些場面的解釋﹐以至我們對《董夫人》某些場面所提出的問題﹐那「解釋」的本身以及那些「問題」的本身﹐也許根本並不重要﹐「解釋」可以改變﹐「問題」可以在某個時候提出來之後再在另一個時候收回﹐那麼重要的應該是什麼呢﹖重要的應該是﹐關於《董夫人》﹐我們的確曾經「討論」過﹐頗為深入地﹐非常認真地就是這一次「討論」的「曾經存在」﹐以及這「討論」本身差不多三個鐘頭的「歷程」﹐這才是真實的﹐重要的﹐下面的記錄﹐便是是次「討論」的企圖重現。
到現在為止我只拍過一部電影﹐我還不是「大作家」。
唐書璇﹕你說杜杜的那篇文章﹐我看過。很坦白說﹐他寫我的唇膏﹐寫我的指甲油﹐等等﹐我的確是不大快樂的。不管你說我是好看還是不好看﹐我都會不大快樂。因為重要的應該是我的工作﹐我的作品﹐而不是我本人﹐尤其﹐不是我的化妝。如果我到夜總會去唱歌﹐寫寫我的化妝﹐那也有點理由﹐現在我又不是到夜總會去唱歌﹐那何必注意我的本人呢﹖
顧耳﹕但是作品不能脫離人生。一個作者在創作的時候﹐或多或少總會把他自己本人的一些東西投射到作品上去﹐所以我們平常談論到它的作者﹐這只是習慣使然吧。

唐書璇﹕可是直到現在為止我實在不以為我已經是一個什麼 personality。我至今只拍過一部電影﹐我還不是「大」作家。《董夫人》不過是我的第一個作品﹐我還有很多很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待我的工作都做得差不多了﹐那時再來談我不遲。當然作品與作者有其必然之關係﹐但即使如此那也應該是關於我的理論﹐我的思想﹐我的看法﹐而不應是我的外貌﹐以至我的化妝。
陸離﹕在你的剪貼薄裡﹐有一個法國記者說你曾拒絕談及你的童年﹐請問你的拒絕是否基於上述同一理由﹖
唐書璇﹕是的。而且有一回差不多開罪了一個法國女記者﹐也是為了這個緣故。我堅持一切皮毛的data對於瞭解作品本身﹐實在沒有什麼用處。如果你問我何年何月何日﹐生於何地﹐家裡有些什麼人﹐在什麼地方讀書﹐這些﹐不是很皮毛嗎﹖
顧耳﹕那麼一件作品與作者過往的人生經驗﹐難道就真的毫無關係了嗎﹖
唐書璇﹕有關係。但是與皮毛的data則無關係。反而可能會使你對我的作品引起誤會﹐不如乾脆只看作品﹐不看人﹐更好一些。如果一定要看一下我﹐作為一個人﹐那麼我的 thoughts﹐feelings﹐theories﹐不是比一切皮毛的data﹐更重要嗎﹖
董夫人殺雞﹐是否過份了﹖
顧耳﹕很好﹐那麼我們現在就直截了當問你一個問題﹐關於《董夫人》﹐請你解答。我們覺得﹐董夫人殺雞那一場﹐似乎不太中國。按照中國傳統﹐即使真有那個感覺﹐那種感情﹐也不一定會用這麼強烈的手法去表現出來。我們中國人一向習慣含蓄﹐意在言外﹐餘韻悠揚﹐不習慣極端與強烈﹐不習慣過分﹐現在董夫人為了發洩﹐卻跑去殺雞﹐這動作的本身﹐會不會太強烈太過分了一點﹖
唐書璇﹕你是指這動作所表現的 emotion﹐還是這動作的 symbolic significance﹖
文世昌﹕兩者都有問題。
唐書璇﹕無論怎樣﹐你總得承認這一場戲﹐始終是 pure cinema。也就是說﹐用音樂﹐用文學﹐用雕塑﹐用繪畫﹐都不可能達到目前已有這個表現形式﹐這也就是 the medium expression。這樣「純電影」的表現方法﹐倘若你說在「電影」裡竟然不方便用﹐甚至說它是過份的強調﹐那麼我只好問你﹕what is cinema﹖
文世昌﹕是這樣。我們覺得﹐你的《董夫人》由頭到尾﹐無論氣氛﹐無論味道﹐都很像印度的薩耶哲雷。只除了殺雞那一場。這殺雞﹐實在太太西方﹐太不夠東方了。
陸離 (默想)﹕特別是滿身鮮血的那個特寫﹐倒好像在薩耶哲雷的電影裡﹐忽然跑了個布紐爾 (Luis Bunuel) 出來。想想﹕布紐爾與薩耶哲雷﹐這可多麼不調和。

唐書璇﹕我也覺得我這個電影很像 Satyajit Ray。但是薩耶哲雷﹐我雖然很 admire 他﹐卻總覺得﹐他應該有更多的勁。他的電影實在不夠勁﹐太 monotonous。
現在說回殺雞那一場。你們說有什麼問題﹐到底是說 method 有問題﹖還是 form 有問題﹖
如果說是 method 有問題﹐那麼無論怎樣﹐到了那一場﹐董夫人既然確實有那麼一個感覺﹐你就總得想個方法﹐找個方法﹐去把那強烈的感覺express出來。如果你不用殺雞﹐你用什麼呢﹖我選擇殺雞﹐因為我覺得它恰當。下面我再解釋為什麼。也許﹐你們根本不曾注意﹐當董夫人殺雞的時候﹐那些雞﹐在戲裡出現﹐已經絕對不是第一次了。在那個時候用到那些雞其實是自然的﹐而不是突然的。
如果你說是form有問題﹐那麼﹐as a form﹐我自己就覺得﹐發展到那裡﹐的確要require something dramatic。好比董夫人在衝出去殺雞之前﹐她在房間裡向房門口衝出去﹐一次又一次﹐重複又重複﹐事實當然不是她果然轉來轉去﹐轉了那麼多次﹐而只是她感覺如此﹐just what she feels﹐這也是pure cinematic expression。
陸離 (默想)﹕董夫人殺雞之前﹐在房間裡「轉身衝向房門口」的那幾下重複 repetition﹐當然安排得很好﹐同時也很美。「美」的意思是說一方面這「動作」重複得很有音樂節奏感﹐另方面盧燕「轉身向前衝」亦轉得美衝得美﹔「好」的意思是說這段膠片不但形式美﹐而且有內涵﹐而且形式與內容結合得很統一。常見這種「重複同一動作」的電影把戲﹐在英國青年導演手中一向出現最多﹐特別是 Richard Lester (一夜狂歡、救命)、Karel Reisz (摩根、一代舞后) 之類﹐但是當他們描寫一個人衝上樓梯而將此動作重複數遍的時候﹐他們總是為了那個beat﹐為了那個rhythm﹐也就是repetition for repetition’s sake﹐而絕少真正的內涵。法國導演記憶中這一下招數則似乎並非他們的名招﹐就有﹐也只是 Alain Resnais 與 Alain Robbe-Grillet 這類導演才像是會用到此一招數的人﹐一直等到《Z》(大風暴)﹐一直等到原籍希臘的 Costa-Gavras﹐才為這一下本來只是用來表現 rhythm 的怪招﹐加添上新的生命。也就是《Z》裡面伊夫蒙丹 (Yves Montand)不治逝世之後﹐他夫人愛蓮琵琶斯 (Irene Papas) 看到醫生用白布覆蓋著丈夫﹐隔著玻璃﹐白布揚起﹐蓋下﹐後來愛蓮琵琶回憶此一動作﹐Costa-Gavras 即將「白布揚起﹐蓋下」重複數遍﹐既有形成美 (音樂節奏感)﹐又有內涵 (沉重、痛心、重要、歷史性的一刻)。如今《董夫人》拍攝于《大風暴》之先﹐那就是唐書璇比 Costa-Gavras 更早一步為這怪招加添上新的生命。
但是﹐但是﹐我們雖然很欣賞董夫人「轉身衝向房門口」的重複﹐我們卻始終依然覺得﹐「殺雞」的這一下「殺」﹐實在是太強烈了 ……
顧耳﹕我們就依照你的意思從method與form的角度來討論吧。先就method說﹐難道真的除了殺雞﹐就沒有其它選擇了嗎﹖在就form說﹐你認為發展至該場﹐必須有些戲劇化的東西﹐可我們就是覺得﹐你整部戲﹐都非常「詩化」﹐到了殺雞﹐卻忽然「戲劇化」起來﹐便是這一下「戲劇化」﹐與前面的「詩化」太不調和﹐簡直有點破壞了前面的「詩化」﹐難道你不曾覺得﹖

唐書璇﹕詩不一定都是靜靜的—-動的、有力的、強烈的﹐也可以是poetry in another form。你們說「殺雞」一場與場面不調和﹐但是我卻反而覺得《董夫人》的好處之一就是consistence of style。為什麼不能有動的詩呢﹖想想﹐「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想想那「動地來」……
顧耳﹕阿﹗那是整個時代﹐董夫人卻只是一個人 ……
唐書璇 (笑) ﹕如此說來也許你根本未曾經驗過什麼叫做frustration!
(顧耳臉紅了)
文世昌﹕你選擇了殺雞這個象徵﹐這雞﹐與中國婦女到底有無傳統上﹐習慣上的關係﹖抑或這個動作﹐十分「佛洛伊德」﹐因此外國人較易接受﹐我們則較難﹖
唐書璇﹕雞與中國婦女﹐當然極有關係。你記得我剛說過﹐當董夫人殺雞的時候﹐那些雞的出現﹐在戲裡其實已經絕對不是第一次。但是現在在談到那些雞之前﹐讓我先講講為什麼外國觀眾可以接受這個中國故事﹐這個中國電影。因為﹐在這個電影裡﹐我通過這個「故事」去表達的﹐本來就是一種human condition﹐一種human feeling﹐這種出現在人與人之間﹐出現在董夫人身上的condition與feeling﹐其實不論何時何地﹐都總會出現,到處是一樣的。因為loneliness﹐以至hope﹐want以至the difficulty in making a choice﹐特別是那loneliness﹐不管你是在大城市裡﹐還是在大森林裡﹐到處都是一樣。就因為我所描寫的human condition 與human feelings﹐到處都是一樣﹐外國觀眾在看到這個電影的時候﹐才會發生共鳴﹐才會有所感受﹐也才會接受這個電影﹐喜歡這個電影。事實上﹐「人」的情況與境遇﹐「人」的感覺與感情﹐豈有不是到處都是一樣的呢﹖只要你能把這境這情﹐真實深銳的表達出來﹐「人」的共鳴又豈會有國籍之分﹖誰聽說過loneliness與frustration是有國界的呢﹖
「貞節牌坊」的故事﹐不過是本片人物的背景而已。我當然知道「貞節牌坊」是個老故事﹐也知道國語片拍過不止一次。但是為什麼別人已經拍過我就不能再拍呢﹖好比畫畫﹐很多人已經畫過了花﹐畫過了山﹐畫過了海﹐這些花、山、海﹐誰能夠說就不能畫了呢﹖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不同的畫法﹐拍電影也是一樣﹐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拍法﹐主要是看你如何去 express。「故事」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特別是那helpless的human con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