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扮嘢 —— They Shoot Nonsense, Don't They ﹖ 1980 年 11 月
我最抵受不住的是那些廿四小時都不斷要把「文藝」掛在口邊的人士。
其實他們只是社會上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在普通的情況下﹐不怎樣容易碰得到﹐但我自己本身也算得上是三分之一個文化人﹐和傳播媒介的人士不多不少有來往﹐上藝術中心亦絕非偶然一次。於是﹐很多時候就會有機會接觸到這輩「一開口就文藝」的人士。
他們大多數是年輕人﹐平均年齡不會超過廿五歲﹐十居其九是剛在各地各類專上學院畢業﹐而且一直對各種文化 / 文藝活動都有一份莫名其妙的狂熱﹔如果有一天香港能一洗「文化沙漠」之嘲﹐這群人居功不少。但我發覺到這群人還有一點不怎樣值得驕傲的共同之處﹐就是他們都不快樂﹐而他們竟藉住一種頗為奇特的方法 —— 展覽自己的智慧﹐去宣洩心中的怨憤﹐向這個世界「報復」。
無可否認﹐他們對事物的態度是充滿嚴肅和認真﹐值得他人敬佩。但有時過分的嚴肅和認真﹐會不會變得走火入魔﹖特別是在「任何」場合﹐對「任何」事物都用同一嚴肅認真的態度時﹐又是否算得上適當﹖而且這些滿嘴文藝的人往往很偏激﹐只要別人在言談間稍為俚俗些﹐表露出玩世不恭﹐或者對 Herzog、和Fassbinder 這些名字毫無反應時﹐就立即展示出厭惡的表情﹐給予鄙視的眼光﹐覺得罪無可恕。總之如果這群人一日不提過 Bertolucci 或者「Ann」的 film sense (他們喜歡叫許鞍華做 Ann﹐和許鞍華幾熟是另外一回事)﹐他們就會渾身不舒服。

阿 Ann!
我對這些人士的心情是頗了解的。他們本來都是充滿理想的年青人﹐在校園內埋頭苦讀了幾年﹐覺得自己已經具備了做「文化人」的條件﹐準備出來社會大幹一番﹐更想得到同路人的重視﹐希望 a star is born 。但往往他們會發覺﹐即使文化圈﹐亦完全不是自己以前想像中那回事﹐別人不單止沒有被他們的「才華」所震驚﹐甚至不怎樣熱衷和他們打交道。雖然每晚他們都去藝術中心鑽﹐也始終鑽不出什麼名堂來﹐而且即使他們千辛萬苦識到「Ann」﹐亦沒有被她熱情地捉住去談三小時《撞到正》的剪接﹔「Joyce 」(我指陳韻文﹐just in case 你不知道) 更不用說﹐簡直當班「小朋友」死嘅﹐和他們講多都無謂。於是這些年青人﹐既不能一嗚驚人,甚至得不到自己心目中偶像的垂青﹐一怒之下便化失望為悲憤﹐誓要作廿四小時 non-stop 的天才曝光。
於是平日閒談間也要運用各種「深奧」的字眼像什麼「層面」、「辯證」、「符號」、「角度」…… 等等似是而非的抽象名詞﹐大聲講出來﹐好叫世人驚異於他們底學養﹔希望能等到有一天﹐譚家明或者舒琪 (對﹐光陰似箭﹐如今舒琪已算是前輩﹐至於陸離等人﹐更早已屬於考古範圍) 會帶著嘆為觀止的眼光﹐轉頭來看看究竟哪一位高手在後面高聲語驚四座。到時這些「滿嘴文藝」就得以一舒長期以來壓抑的悶氣﹐獲得一陣滿足的快感﹐覺得他們終於 made a presence。
當然﹐想等這一天的來臨﹐簡直是遙遙無期。事實上﹐「滿嘴文藝」的「智慧」﹐即使不斷自我散播﹐亦依然沒有引起想像中的轟動﹐因為他們不是天才﹐天才通常是很少出聲的﹐更加不會滿嘴文藝。他們只不過是看了一些很多人在他們的年紀早已看過的「學術性」書籍。最巴閉﹐也大概是他們最近在外國看了幾部香港尚未公映的「藝術片」﹐或者看多了一些「前衛藝術」。他們可能很聰明﹐但實在沒有什麼值得別人大驚小怪之處。而且為什麼他們總是要 take everything so seriously﹖對自己﹐對別人都缺乏幽默感。他們不擇手段﹐不顧一切去文藝﹐更加惹起別人的反感﹐甚至會在背後偷偷笑他的「戇居」。
他們為什麼總不能明白到 there's a time for everything﹐有時我們可以嚴肅地討論第一映室最近放映的一系列蘇聯片﹐但有時我們也可以研究一下 (歡樂今宵) 的陳儀馨究竟是不是鬼頭仔﹐專門向上頭打小報告。
有一次連詹小萍也忍不住要問一位超級「滿嘴文藝」可不可以用些比較conversational 的語氣談話﹗我的意思是﹕詹小萍的丈夫是梁濃剛﹐一個 no nonsense 廿四小時都要學究的人。如果連日夜被梁濃剛薰陶的詹小萍也受不住﹐這位仁兄的文藝「功力」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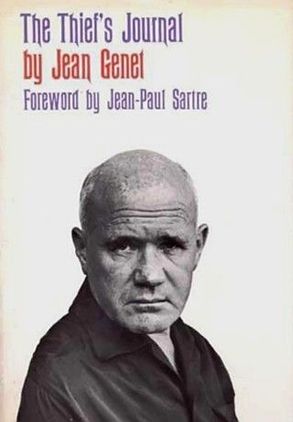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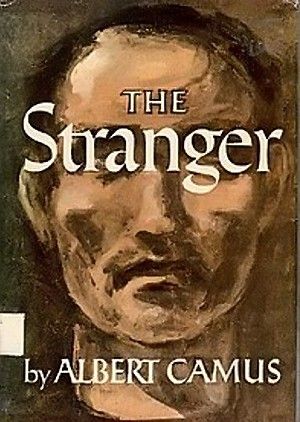
其實滿口文藝可以說是一種不成熟的表現﹐就我自己來說﹐很慚愧﹐很後悔﹐也曾經過這個階段。以前讀中學的時候﹐總是喜歡拿看一本卡繆﹐或者一本沙特、卡夫卡、Genet (英譯文) 隨街走﹐或者拿著一張 Edith Piaf、 Charles Aznavour 的唱片搏被人見到﹐現在想起來就面紅。記得在美國唸書時有一次我和一個「文藝」朋友在飯堂用文藝餸飯﹐剛巧有個戲劇系的同學行過﹐和我們打招呼﹐並順口問我們對最近上映的一套musical 電影的意見。我們兩個就立即 blah blah blah 地大談那套電影缺乏「藝術性」﹐怎樣沒有「深度」﹐如何「做作」。對著我們和堆在我們面前的意大利粉、可樂、cheese cake、雪糕、薯條﹐他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只得禮貌地和我們點點頭﹐說﹕「我要先行了﹐你們繼續談你們的藝術吧。」當時我聽了倒沒有什麼感覺﹐但現在想落﹐就覺得當時的舉動實在太幼推﹐羞死人。還有我唸書時﹐千辛萬苦找張安娜卡蓮娜 poster 貼在牆上﹐讓朋友、同學進來看到﹐問我﹕「她是誰﹖」然後﹐我慢條斯理地回答﹕「Anna Karina﹐the ex-wife of Jean-luc Godard。」他們聽了依然一頭霧水﹐而我卻得到一陣優越感。天啊﹐為什麼當年我會是那麼淺薄、荒謬﹖如果我能夠再活多一次﹐該多好﹗

這就是我當年在宿舍房中貼上的 Anna Karina
但我認為﹐雖然「滿嘴文藝」是某些人成長過程中必經的階段﹐只要得到適當的勸告和輔導﹐這個階段是可以跨越的﹐不用將來成熟的時候﹐像我,要為當初的幼稚而感到羞恥。我認識有些真正有學問的朋友﹐他們年少的時候﹐都沒有經過「滿嘴文藝」的階段﹐像丘世文﹐他是少數我認為真正「有料」而我又衷心佩服的人﹐但他不會無故在人面前談文說藝﹐甚至極力避免﹐不讓人知道他底令人大吃一驚的修養。而我另一個朋友更矯枉過正﹐每次看完第一映室﹐就必定以最快速度遠離藝術中心﹐慌死給人見到。
比起他們﹐我就平庸得多了﹐但我終於都能夠明白﹕雖然 I really learnt it the hard way。故此﹐我希望那些「滿嘴文藝」的小朋友們﹐能做一點反省功夫﹐盡可能節制自己談文說藝的衝動。與其隨口入隨口出﹐不如先放入裏面好好消化﹔人生那麼長﹐哪怕將來用不著﹖
而且﹐應該對自己說﹕Who the hell are 譚家明和舒琪 anyway﹗
上一篇:E-06 由演員變成明星 — 對近期文化圈的一點感想
下一篇:E-08 埋葬苦學生
